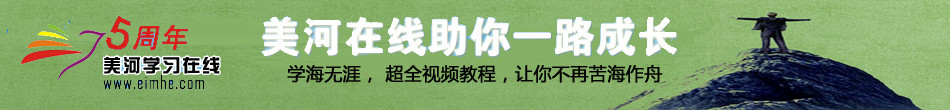思想内容述评:
& p" a3 t {8 C. a' N/ p( ]4 Y) Z G& Z! z9 G E
作为一篇艺术作品,本文确可以称之为“美文”了,但从思想内容分析,似乎还相当复杂,难以一言概之。3 T, M& W, j+ u9 C0 a! X
“五四”运动的落潮,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逐渐分化,使朱自清感到迷茫、苦闷、彷徨。他不满现实,却又无力反抗;想寻出路,却又四顾茫茫。“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正是他的处境的生动写照。这种心情与状况,在作者的另文《那里走》中表达得十分直截了当:“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法。”于是,作者避到南京来了,于是,他为“六朝遗迹”所吸引,来秦淮河上怀古探趣,躲避尘世间的烦恼来了。这时他的情绪,如他给俞平伯的信中所说:“极感到诱惑底力量,颓废底滋味,与现代的懊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残信》)& a! s- V6 {1 u
综观全文,可以发现,上述这种情绪在作者行文中随处可见。
: u& S. `; F2 q w, w' I) D/ M 作者游秦淮河,本是一种彷徨中的挣扎,苦闷中的自我解脱。所以,他努力地从桨声、小船、灯影、波光中去寻求乐趣,聊以自慰。可是,他实在无从超脱,难以忘情。故桨声灯影乍起,明漪薄霭一现,他便被渐渐的引入美梦了。于是,梦境又与心境连在一起了;于是,六朝繁华,秦淮艳迹,便一齐在梦中显现,乃至于“满船成了历史的重载了”,乃至于“愁梦太多了”,小船“如何载得起呀?”从这“重载”和载不起的“梦”,人们不难体察到作者的心情之沉重和纷乱。在这里,眼前与梦幻,历史与现实,美景与愁怀,正是恰到妙处地、曲折地把朱自清那种企图“忘却现代的懊恼”,追求暂时宁静的动机,以及时时又摆脱不了、忘怀不了的烦恼之状,含蓄地蕴藉地表现出来了。
L' ]4 ?1 g8 e1 x3 i 如果说上述心绪还只是淡淡地隐隐约约地显露的话,那么从妓船的出现,歌妓们再三相邀买唱的事情发生后,作者的这种心理状态便暴露无遗。本来,作者以为歌妓已被取缔,却“不料她们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为此他甚觉“同情”,而对方一再地兜生意,乃至“纠缠”到自己身上,作者不禁有些“张皇”:因为“道德律的压迫”,他不愿点歌,而又因为拒绝点歌使对方的“希望受了伤”,且又因为盼望昕歌,“憧憬贴耳的妙音”,以至“理智与情感发生冲突”,不由得“盘旋不安,起坐不宁”;景因情变,他那无法排遣的烦恼与苦闷,透过对夜色的描写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了。( D. `6 M6 E1 E$ b
郁达夫在《现代散文导论(下)》中谈到朱自清的散文时曾说:“作者处处不忘自然,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本文先由自然之景而喜,却又喜中含忧;尔后又因社会之景而忧,进而不安、怅惘、幻灭;这就生动、深刻地勾勒了一个在黑暗中探求出路,并时时“惆怅着过去,忧愁着将来”(923年1月13日残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复杂迷惘的处境和心态。
& _: ^5 \/ ]0 {* r) d7 d. [7 _* c3 |% X j, A+ w( {. \" L
- N0 d" s' ^* ]
8 v+ V* `% F, m: M: u: M ^8 h( ]3 P) c$ I9 o1 \! A
1 N: I( Y* N; ^, V: X8 ]) J
9 I5 U$ O3 `; [- l: k) d
; g0 A; h8 J) v, D
3 x1 j2 t$ ~+ T" c6 z, X. |5 y, G: u |
/ W% y5 m2 w+ X( \9 _/ b$ b艺术特色举要:! f, _% p" | o, s0 C6 T
9 u% d# o& f M! H8 N; F 本作品的第一个显著特色是情景交融。2 q. C! K0 T+ y9 [
第一部分,作者偏重于写景。然而,如上所述,游景本身是为了排遣愁情。所以,赏景之中,见景生情,悠然入梦,而又因梦缘情,这一句句,一笔笔皆写得十分细腻,自然。尔后,作者从情怀中摆脱出来,继续赏景,那“月色”、“微风”、“白云”、“灯辉”,使作者的心情转而又喜,又生发“天厚我们”的议论,这景与情便水乳般地融合在一起了。
' y; O0 j: k# J2 U0 G3 _ 同样,在第二部分中,作品重在抒情。首先,作者写歌妓卖唱一事。因事缘情,发了许多议论感慨。由于对处理此事的矛盾心情,作者于心不安乃至于决定归去。此刻,美景因情“减色”,月光“冷”了,水影“黑”了,舟儿“孤”了,汩——汩——的桨声,几乎要“睡”了……这景因情移的描写堪称绝妙。
5 G8 J" X: W" G; Q. d1 s7 v' O 王夫之《姜斋诗话》云:“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正是如此。
# W( _" x& q( H 作者描写游南京秦淮河所见景色,给我们展示了一幅绝妙的工笔画。虽然水色、天光、月态、灯彩、人影、船形、树姿、琴声、歌音等都是人们常见而易于忽略的事物,但作者善于把它们都错杂起来作“加倍”的描写,因此写得很细腻,精密确切地写出了当时秦淮河上那一种灯月交辉、画舫纵横、笙歌彻夜的景象。写夏夜泛舟游秦淮河,自然离不开写水,也离不开写天上的月、船上的灯。所以作者特别注意对月亮、灯光、河水三者关系的变化,作细针密线的描绘和渲染,逼真地表现出当时当地所独具,又是作者凭着自己的审美趣味最能领略的美的境界。你看,这是夜幕方垂,灯火初明时的情景:“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这是着意灯光,描绘灯光在水中的投影。那么水呢?水在天未断黑时,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可是到灯火初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象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这是着意水态,展现灯明前后水的色泽意态的变幻。作者还通过那水中灯影和灯下水光的描写,表现了当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图景。因为这时皎月初升,光量不大,所以灯光压倒了月色,灯火透过玻璃投射到黯淡的水波里,河里便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烟霭”,构成一种梦幻般的迷离境界,从而惹起人们思古之幽情。
+ ^) w$ {& F* [ 朱自清的一些描写山水的名文,也都寄寓着他的人生态度,反映了某种人生。《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不例外,不只在它所描写的秦淮河的桨声、灯影、薄霭和微漪,更在于它让人想起《桃花扇》及《板桥杂记》所载的“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历史的影象使然了。”秦淮河热闹的景象中夹杂着“被逼以歌为业”的歌妓的卖笑生涯,虽则“卖歌和卖淫不同”,对她们的身世,我们“究竟应该同情的”,所以当听到“一只载妓的板船”经过时传来的响亮而圆转的清歌,清游中的作者,却感到了寂寞。散文的结尾用繁笔抒写了游后船里满载的怅惆和心里充满的幻灭的情思。今日的秦淮河繁华、哀伤,一如明末。繁华的景象留给作者的是哀愁,而这哀愁又来自于对繁华背后的不幸人生的同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写景的名文,更是抒情的名文,融情入景,以情见长,是朱自清散文风格的艺术特征。& s e5 w% Z0 C0 N- u7 H
本文另一个重要特色便是语言优美。" u- G1 O: m" W# n
“秦淮河的船,比北京万牲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这几处的船不是觉着笨,就是觉着简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们的情韵,如秦淮河的船一样。”这一节不由得令人想到作者另一个散文名篇《绿》。这种慢慢地细细地娓娓地比较式的叙写,晓畅平易,凝炼概括,具有一种和谐的韵味。+ \ Z% A* w4 Q9 n; Q' T
同样,“那晚月儿已瘦削了两三分。她晚妆才罢,盈盈的上了柳梢头。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这里,生动的比拟,形象的比喻,细致的描绘,几乎已达到了维妙维肖的地步,读来像画。作者本人认为:“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画。他的叙事、抒情、写景,固然是画;就是说理,也还是画。”(《山野缀拾》)可见,作者是善于捕捉、表现语言的绘画美的高手。
* q4 m: R3 W% g0 v 此外,作品用典雅丽、炼词炼字精当,也为语言的美妙增辉不少。8 n: S. k' a2 m8 s9 m! @" `3 Y8 T5 D
: ]2 N6 y0 ~: Z! o- w
- q% {( q9 l' @6 A: ^$ z3 L
- Y# u$ i* G+ y( R, w
: z2 G. I7 _) ]. t# t! c
0 }# B- B, R5 W& r+ D$ ^. _. u6 t6 o8 T1 @" k
; `3 _6 K, P$ f- ]; H' U4 b) N' a+ p
层次结构剖析 1 a' t" d, a2 M& G) ?7 I2 q' b; M
% W& ?& F- s9 t. q6 |; A 本文结构,从总体布局看,全文可一断为二:前半部分,作者倾笔写的是船、桥、灯、水、月、天……在这里,景是自然之景,天然之景,人只是景中的一个点缀。作者舒闲地从赏析者、旁观者的角度去察视、体会景中之味。但却未曾与景中之物发生直接的关系,与景中之人发生直接的对话;换言之,作者是受美景之陶冶,被美景所沉醉,颇有悠然自得、如入世外桃源之状。而后半部分,作者的情趣兴味已与前大不相同。因为河上有一种歌妓,驾着小船,到处兜拉生意,来了一只,被“受道德律的压迫”而不愿狎妓(即使是歌妓)的作者抱歉地拒绝了,受了三次窘。虽说那歌声是美妙的,甚至有点受之“诱惑”和“降服”,但听歌却又感到内心的不安和踌躇,这就生发了许多矛盾的思想,由此而怅惘到终篇。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叙及的几乎全是社会之状,社会之态。与之发生直接对话与联系的是人,是那些歌妓。虽说作者想竭力地回避社会现实,然而却难以超然,这就引出了许许多多的烦恼。
; g+ A' e* ]$ ?1 J4 f 两大部分,前者是“出”,由景牵情而去;后者是“入”,由人由事带情而来。前后之间,以情暗贯全篇,布局对应、工整,构思之匠心自见。
% x; w$ |% L. u, ~0 s; Y 从具体的结构层次安排看,两大部分,各自又围绕着不少对应点来写,层次间的互扣互联甚紧。+ N( Q _& k2 A$ g! s+ i* {" q# n5 T! W
第一部分中,作者由“桨声灯影”出发,写船、写水、写天、写月、写歌……一是“声”,一是“影”,无不融入其中;这是视觉与听觉互为对应。朱先生是知识分子,博古通今,多愁善感。每见一景,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历史,想到六朝金粉,想到明末艳迹,想到《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之所载,想到秦淮河极盛时期的繁华……在这里,过去与现在,兴亡盛衰之叹,又是一组对应。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曾多次恍若入梦:黯淡的水光,像梦;闪烁的灯光,像梦的眼睛;桥,“有些虚无缥缈”,水,“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幕似的”;这种感觉,甚至一直延伸到结尾:倦得又要入梦,却是最后的梦,最短的梦!现实与梦境的对应,显而见之。
, y) i/ l6 m& [5 f# K1 I: u 第二部分中,作者的这种比较、对应的层次铺排是通过人与人、人与事的矛盾关系来叙写的:歌妓要兜生意,作者与同伴却予以拒绝;那歌声确实是美妙的,而道德律却不允许作者欣赏;一再的回绝当然引起对方的不快,作者于心不忍却又无可奈何;河面繁荣喧嚣,歌声人语热闹,然作者却感到懊悔、怅惘乃至幻灭。现实(眼前的人、事、景)与精神(心中的思想、情绪、感触)呈现一种互为矛盾的对应。
' r9 X! Y, t( L) g2 j 就这样,全文的篇章、段落、层次、首尾、上下、前后,缜密地互为对立而又相互对应,构成了一个和谐完整的艺术整体。 |